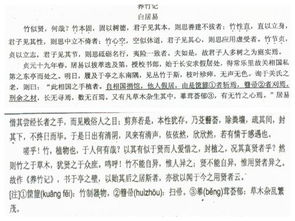文言文翻译暴之于民(“暴之于民而民受之”的翻译)
1.“暴之于民而民受之”的翻译
梁惠王说:“我治理魏国,真是费尽心力了。黄河北岸的地方遇到饥荒,我便把那里的百姓迁移到黄河以东的地方,同时把黄河以东地方的粮食运到黄河以内的地方。黄河以东的地方遇到饥荒,也这样办。我曾经考察过邻国的政事,没有谁能像我这样尽心的。可是,邻国的百姓并不因此减少,我的百姓并不因此加多,这是什么缘故呢?”
孟子回答说:“大王喜欢战争,那就请让我用战争打个比喻吧。战鼓冬冬敲响,枪尖刀锋刚一接触,有些士兵就抛下盔甲,拖着兵器向后逃跑。有的人跑了一百步停住脚,有的人跑了五十步停住脚。凭借跑了五十步的士兵,竟耻笑跑了一百步的士兵,可以吗?”
惠王说:“不可以。只不过他们没有跑到一百步罢了,但这也是逃跑呀。”
孟子说:“大王如果懂得这个道理,那就不要希望百姓比邻国多了。
如果兵役徭役不妨害农业生产的季节,粮食便会吃不完;如果细密的渔网不到深的池沼里去捕鱼,鱼鳖就会吃不光;如果按季节拿着斧头入山砍伐树木,木材就会用不尽。粮食和鱼鳖吃不完,木材用不尽,那么百姓便对生养死葬没有什么遗憾。百姓对生养死葬都没有遗憾,就是王道的开端了。
分给百姓五亩大的宅园,种植桑树,那么,五十岁以上的人都可以穿丝绸了。鸡狗和猪等家畜,百姓能够适时饲养,那么,七十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吃肉了。每家人有百亩的耕地,官府不去妨碍他们的生产季节,那么,几口人的家庭可以不挨饿了。认真地办好教育,反复地用孝顺父母、尊敬兄长的大道理教导老百姓,那么,须发花白的老人也就不会自己背负或顶着重物在路上行走了。七十岁以上的人有丝绸穿,有肉吃,普通百姓饿不着、冻不着,这样还不能实行王道,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。
现在的梁国呢,富贵人家的猪狗吃掉了百姓的粮食,却不约束制止;道路上有饿死的人,却不打开粮仓赈救。老百姓死了,竟然说:‘这不是我的罪过,而是由于年成不好。’这种说法和拿着刀子杀死了人,却说‘这不是我杀的而是兵器杀的’,又有什么不同呢?大王如果不归罪到年成,那么天下的老百姓就会投奔到梁国来了。”

2.“荐之于天而天受之,暴之于民而民受之”的意思 搜狗问问
请问推荐给天,天接受了;公开介绍给老百姓,老百姓也接受了是怎么回事呢?”
孟子说:“叫他主持祭祀,所有神明都来享用,这是天接受了;叫他主持政事,政事治理得很好,老百姓很满意,这就是老百姓也接受了。天授与他,老百姓授与他,所以说,天子不能够拿天下授与人。舜辅佐尧治理天下二十八年,这不是凭一个人的意志够做得到的,而是天意。尧去世后,舜为他服丧三年,然后便避居于南河的南边去,为的是要让尧的儿子继承天下。可是,天下诸侯朝见天子的,都不到芜的儿子那里去,却到舜那里去;打官司的,都不到尧的儿子那里去,却到舜那里去;歌颂的人,也不歌颂尧的儿子,却歌颂舜。所以你这是天意。这样,舜才回到帝都,登上了天于之位。如果先前舜就占据尧的宫室,逼迫尧的儿子让位,那就是篡夺,而不是天授与他的了。《太誓》说过:‘上天所见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见,上天所听来自我们老百姓的所听。’说的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3.《信,君之大宝》文言文译文
【文言文原文】
《资治通鉴》(一)·资治通鉴第二卷
臣光曰:夫信者,人君之大宝也。国保于民,民保于信;非信无以使民,非民无以守国。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,霸者不欺四邻,善为国者不欺其民,善为家者不欺其亲。不善者反之,欺其邻国,欺其百姓,甚者欺其兄弟,欺其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离心,以至于败。所利不能药其所伤,所获不能补其所亡,岂不哀哉!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,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,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,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。此四君者道非粹白,而商君尤称刻薄,又处战攻之世,天下趋于诈力,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,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!
【白话文译文】
臣司马光曰:信誉,是君主至高无上的法宝。国家靠人民来保卫,人民靠信誉来保护;不讲信誉无法使人民服从,没有人民便无法维持国家。所以古代成就王道者不欺骗天下,建立霸业者不欺骗四方邻国,善于治国者不欺骗人民,善于治家者不欺骗亲人。只有蠢人才反其道而行之,欺骗邻国,欺骗百姓,甚至欺骗兄弟、父子。上不信下,下不信上,上下离心,以至一败涂地。靠欺骗所占的一点儿便宜救不了致命之伤,所得到的远远少于失去的,这岂不令人痛心!当年齐桓公不违背曹沫以胁迫手段订立的盟约,晋文公不贪图攻打原地而遵守信用,魏文侯不背弃与山野之人打猎的约会,秦孝公不收回对移动木杆之人的重赏,这四位君主的治国之道尚称不上完美,而公孙鞅可以说是过于刻薄了,但他们处于你攻我夺的战国乱世,天下尔虞我诈、斗智斗勇之时,尚且不敢忘记树立信誉以收服人民之心,又何况今日治理一统天下的当政者呢!
4.古文翻译 孟子*梁惠王下(节选)
(一)庄暴见孟子①,曰:“暴见于王②,王语暴以好乐,暴未有以对也。”
曰:“好乐何如?” 庄暴来见孟子,说:“我被齐王召见,齐王告诉我,他喜爱音乐,我没有话回答他。”庄暴问道:“喜爱音乐怎么样?”孟子曰:“王之好乐甚,则齐国其庶几乎!” 孟子说:“(如果)齐王非常喜爱音乐,齐国恐怕就有希望了!”他日,见于王曰:“王尝语庄子以好乐,有诸?” 后来的某一天,孟子被齐王接见,问(齐王)道:“大王曾对庄暴说喜爱音乐,有这回事吗?”王变乎色,曰:“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,直好世俗之乐耳。”
齐王(不好意思地)变了脸色,说:“我不是喜爱古代先王的音乐,只是喜爱世俗的音乐罢了。”曰:“王之好乐甚,则齐其庶几乎!今之乐由古之乐也。”
孟子说:“大王非常喜爱音乐,齐国恐怕就有希望了!现在的音乐如同古代的音乐。”曰:“可得闻与?” 齐王说:“可以把道理讲给我听听吗?”曰:“独乐乐,与人乐乐,孰乐?” 孟子问:“一个人欣赏音乐的快乐,与别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,哪一种更快乐?”曰:“不若与人。”
齐王说:“不如同别人一起欣赏快乐。”曰:“与少乐乐,与众乐乐,孰乐?” 孟子问:“同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,同很多人一起欣赏音乐的快乐,哪一种更快乐?”曰:“不若与众。”
齐王说:“不如同很多人一起欣赏快乐。”“臣请为王言乐。
今王鼓乐于此,百姓闻王钟鼓之声,管龠之音③,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④:‘吾王之好鼓乐,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?父子不相见,兄弟妻子离散。’今王田猎于此,百姓闻王车马之音,见羽旄之美⑤,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:‘吾王之好田猎,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?父子不相见,兄弟妻子离散。
’此无他,不与民同乐也。 (孟子说:)“请让我为大王谈谈音乐。
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,百姓听了大王钟鼓的声音,箫笛的曲调,全都头脑作痛,眉头紧皱,互相议论说:‘我们君王喜爱音乐,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样的极点?父子不能相见,兄弟妻儿离散。’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,百姓听到大王车马的声音,看到旗帜的华美,全都头脑作痛,眉头紧皱,互相议论说:‘我们君王喜欢打猎,为什么使我们痛苦到这样的极点?父子不能相见,兄弟妻儿离散。
’这没有别的原因,是不和百姓共同快乐的缘故。今王鼓乐于此,百姓闻王钟鼓之声,管龠之音,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: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,何以能鼓乐也?’今王田猎于此,百姓闻王车马之音,见羽旄之美,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:‘吾王庶几无疾病与,何以能田猎也?’此无他,与民同乐也。
今王与百姓同乐,则王矣。” 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奏乐,百姓听到钟鼓的声音,箫笛的曲调,都欢欣鼓舞,喜形于色,互相议论说:‘我们君王大概没什么病吧,不然怎么能奏乐呢?’假设现在大王在这里打猎,百姓听到君王车马的声音,看到旗帜的华美,都欢欣鼓舞,喜形于色,互相议论说:‘我们君王大概没什么病吧,不然怎么能打猎呢?’这没有别的原因,是和百姓共同快乐的缘故。
如果大王能和百姓共同快乐,那就能称王于天下了。” [注释] ①庄暴:齐国大臣。
②王:指齐宣王。③管龠(yuè):古管乐器名。
龠,似笛而短小。④蹙頞(cù è):蹙,紧缩;頞,鼻梁。
蹙頞,形容愁眉苦脸的样子。⑤羽旄:鸟羽和旄牛尾,古人用作旗帜上的装饰,故可代指旗帜。
5.谁有 唐玄宗戒酒 这篇文言文的译文
是臣之所慰荐,以至荣 达.臣之子愚,谓知古见德,必容其非,故必干之."上于是 明崇不私其子之过,而薄知古之负崇也.上欲斥之,崇为之请 曰:"臣有子无状,挠陛下法,陛下特原之,臣为幸大矣.而 犹为臣逐知古,海内臣庶必以陛下为私臣矣,非所以俾元化也. 次柳氏旧闻 3 "上久乃许之.翌日,以知古为工部尚书,罢知政事. 源乾曜因奏事称旨,上悦之,于是骤拔用,历户部侍郎, 京兆尹,以至宰相.异日,上独与力士语曰:"尔知吾拔用乾 曜之速乎 "曰:"不知也."上曰:"吾以其容貌,言语类 萧至忠,故用之."力士曰:"至忠不尝负陛下乎陛下何念之 深也 "上曰:"至忠晚乃谬计耳.其初立朝,得不谓贤相乎 "上之爱才宥过,闻者无不感悦. 萧嵩为相,引韩休为同列.及在位,稍与嵩不协,嵩因乞 骸骨,上慰嵩曰:"朕未厌卿,卿何庸去 "嵩俯伏曰:"臣 待罪相府,爵位已极,幸陛下未厌臣,得以乞身.如陛下厌臣, 臣首领之不保,又安得自遂 "因陨涕.上为之改容,曰:" 卿言切矣,朕思之未决.卿第归,至夕当有使.如无使,旦日 宜如常朝谒也."及日暮,命力士诏嵩曰:"朕惜卿,欲固留, 而君臣始终,贵全大义,亦国家美事也.今除卿右丞相."是 日,荆州始进柑子,上以素罗包其二以赐之. 玄宗好神仙,往往诏郡国征奇异士.有张果者,则天时闻 其名,不能致.上亟召之,乃与使偕至.其所为,变怪不测. 又有刑和璞者,善算心术视人,投算而能究知善恶夭寿.上使 算果,懵然莫知其甲子.又有师夜光者,善视鬼,后召果与坐, 密令夜光视之.夜光进曰:"果今安在臣愿得见之."而果坐 于上前久矣,夜光终莫能见.上谓力士曰:"吾闻奇士至人, 外物不足以败其中,试饮以堇汁,无苦者乃真奇士也."会天 寒甚,使以汁进果.果遂饮,尽三卮,醇然如醉者,顾曰:" 非佳酒也."乃寝.顷之,取镜视其齿,已尽焦且黧矣.命左 右取铁如意以击齿,尽堕,而藏之于带.乃于怀中出神药,色 微红,傅于堕齿穴中.复寝.久之视镜,齿皆生矣,而粲然洁 白,上方信其不诬也. 次柳氏旧闻 4 玄宗尝幸东都,天大旱且暑.时圣善寺有竺乾僧无畏,号 三藏,善召龙致云之术.上遣力士疾召无畏请雨,无畏奏云: "今旱,数当然耳.召龙兴云,烈风迅雷,适足暴物,不可为 也."上强之曰:"人苦暑病矣.虽暴风疾雷,亦足快意." 无畏不得已.乃奉诏.有司为陈请雨具,而幡幢像设甚备.无 畏笑曰:"斯不足致雨."悉令撤之.独盛一钵水,以刀搅旋 之,胡言数百咒水.须臾有如龙状,其大类指,赤色,首啖水 上,俄复没于钵水中.无畏复以刀搅水,咒者三.顷之,白气 自钵中兴,如炉烟,径上数尺.稍引去,出讲堂外.无畏谓力 士曰:"宜去,雨至矣."力士绝驰而去,还顾见,白气疾旋, 自讲堂西岩一匹素者.既而昏霾,大风震雷以雨.力士才及天 津之南,风雨亦随马而驰至矣,衢中大树多拔.力士比复奏, 衣尽沾湿.时孟温礼为河南尹,目睹其事.温礼子皞,尝言于 臣亡祖先臣,与力士同.吏部员外郎李华撰《无畏碑》,亦云 奉诏致雨,灭火风,昭昭然遍于耳目也.今洛京天津桥 有荷泽寺者,即高力士去请咒水祈雨,回至此寺前,雨大降, 明皇因于此地造寺,而名荷泽焉.寺今见存 玄宗善八分书,凡命将相,皆先以御札书其名,置案上. 会太子入侍,上举金瓯覆其名,以告之曰:"此宰相名也,汝 庸知其谁耶射中,赐尔卮酒."萧宗拜而称曰:"非崔琳,卢 从愿乎 "上曰:"然."因举瓯以示之,乃赐卮酒.是时, 琳与从愿皆有宰相望,玄宗将倚为相者数矣,终以宗族繁盛, 附托者众,卒不用. 肃宗在东宫,为李林甫所构,势几危者数矣.无何,鬓发 斑白.常早朝,上见之,愀然曰:"汝第归院,吾当幸汝." 及上至,顾见宫中庭宇不洒扫,而乐器久屏,尘埃积其间,左 右使命,无有妓女.上为之动色,顾力士曰:"太子居处如此, 次柳氏旧闻 5 将军盍使我闻之乎 "上在禁中,不名力士,呼为"将军". 力士奏曰:"臣尝欲上言,太子不许,云:无以动上念."上 即诏力士下京兆尹,亟选人间女子细长洁白者五人,将以赐太 子.力士趋出庭下,复还奏曰:"臣他日尝宣旨京兆阅致女子, 人间嚣嚣然,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为口实.臣以为掖庭中故衣 冠以事没其家者,宜可备选."上大悦,使力士诏掖庭,令按 籍阅视.得三人,乃以赐太子,而章敬皇后在选中.顷者,后 侍寝,厌不寤,吟呼若有痛,气不属者.肃宗呼之不解,窃自 讦曰:"上始赐我,卒无状不寤.上安知非吾护视不谨耶 " 遽秉烛视之.良久方寤.肃宗问之,后手掩其左胁曰:"妾向 梦有神人长丈余,介金操剑,谓妾白:'帝命吾与汝作子.' 自左胁以剑决而入腹,痛殆不可忍,及今未之已也."肃宗验 之于烛下,有若綖而赤者存焉.遽以状闻,遂生代宗.吴操尝 言于先臣,与力士说符. 代宗之诞三日,上幸东宫,赐之金盆,命以浴.吴皇后年 幼体弱,皇孙体未舒,负媪惶惑,乃以宫中诸子同日生,而体 貌丰硕者以进.上视之不乐曰:"此非吾儿."负媪叩头具服. 上睨谓曰:"非尔所知,取吾儿来."于是以太子之子进见. 上大喜,置诸掌内,向日视之,笑曰:"此儿福禄一过其父." 及上起还宫,尽留内乐,谓力士曰:"此一殿有三天子,乐乎 哉!可与太子饮酒."吴溱尝。
6.这段文言文怎么翻译
原文:
鬬且廷见令尹子常,子常与之语,问蓄货聚马。归以语其弟,曰:“楚其亡乎!不然,令尹其不免乎。吾见令尹,令尹问蓄聚积实,如饿豺狼焉,殆必亡者也。
“夫古者聚货不妨民衣食之利,聚马不害民之财用,国马足以行军,公马足以称赋,不是过也。公货足以宾献,家货足以共用,不是过也。夫货、马邮则阙于民,民多阙则有离叛之心,将何以封矣。
“昔鬬子文三舍令尹,无一日之积,恤民之故也。成王闻子文之朝不及夕也,于是乎每朝设脯一束、糗一筐,以羞子文。至于今秩之。成王每出子文之禄,必逃,王止而后复。人谓子文曰:‘人生求富,而子逃之,何也?’对曰:‘夫从政者,以庇民也。民多旷者,而我取富焉,是勤民以自封也,死无日矣。我逃死,非逃富也。’故庄王之世,灭若敖氏,唯子文之后在,至于今处郧,为楚良臣。是不先恤民而后己之富乎?
“今子常,先大夫之后也,而相楚君无令名于四方。民之羸馁,日已甚矣。四境盈垒,道殣相望,盗贼司目,民无所放。是之不恤,而蓄聚不厌,其速怨于民多矣。积货滋多,蓄怨滋厚,不亡何待。
“夫民心之愠也,若防大川焉,溃而所犯必大矣。子常其能贤于成、灵乎?成不礼于穆,愿食熊蹯,不获而死。灵不顾于民,一国弃之,如遗迹焉。子常为政,而无礼不顾甚于成、灵,其独何力以待之!”
期年,乃有柏举之战,子常奔郑,昭王奔随。
(选自《国语·楚语》)
译文:
鬬且在朝廷见了令尹子常,子常和他谈话,询问怎样才能聚敛财宝和马匹。鬬且回家后告诉了他的弟弟,说:“楚国恐怕要灭亡了吧!如果不是这样,令尹恐怕不免于难。我见到令尹,令尹询问怎样积聚财宝,像饥饿的豺狼一样,恐怕是一定要败亡的。
“古时候积聚财货不妨害百姓衣食的利益,聚敛马匹不损害百姓的财物,国家征收的马匹能满足行军所用,公卿的戎马能与兵赋的需要相称,不超过这个限度。公卿的财货足够馈赠贡献所用,大夫家的财货足够供给使用,不超过这个限度,财货与马匹过多百姓就会穷困,百姓过于穷困就会产生背叛之心,那凭什么来立国呢?
“以前鬬子文三次辞去令尹的职务,家里没有一天的储粮,是由于体恤百姓的缘故。楚成王听说子文吃了早饭就没有晚饭,因此每逢朝见时就准备一束肉干、一筐粮食,用来送给子文。直到现在已成为对待令尹的惯例。成王每次颁下子文的俸禄,子文一定要逃避,等到成王不再这样做,然后他才回来任职。有人对子文说:‘人活着都追求富贵,但您却逃避它,为什么呢?’子文回答说:‘从政的人,是保护人民的。民众都很贫困,而我却取得富贵,这是劳苦了百姓而使自己富厚,不知哪天就会遭祸而死了。我是逃避死亡,不是逃避富贵。’所以楚庄王在位的时候,灭掉了若敖氏家族,只有子文的后代还在,一直到现在还住在郧地,做楚国的良臣。这不是首先体恤百姓然后自己才富有吗?
“现在子常,是先大夫的后代,辅佐楚国国君却在四方没有好名声。百姓饥瘦挨饿,一天比一天更厉害了。四周边境布满了堡垒,道路上饿死的人到处可见,盗贼张目窥伺,民众无所依靠。他不去顾恤这些,反而聚敛不已,招致民众怨恨的太多了。积累的财货越多,蓄积的怨恨也就越深,不灭亡还等待什么?
“对待百姓心中的愤怒,就像堤防大河一样,一旦崩溃了破坏一定很大。子常的下场能比成王和灵王好吗?成王对穆王无礼,临死时想吃熊掌,都没有得到就死了。灵王不顾百姓死活,全国的人都抛弃了他,就像丢下脚印一样。子常执政,他对别人的无礼和不顾百姓死活,比成王、灵王还厉害,他独自一个人有什么力量来抵御呢?”
一年以后,就发生了柏举之战,子常逃亡到了郑国,楚昭王逃到随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