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解事仆射文言文翻译(求《资治通鉴)
1.求《资治通鉴
你这个比较长啊~原文不大好找,我估计只找到了一部分的原文,你看还缺了哪里吧太元7年,冬天的十月。秦王苻坚和大臣们在太极殿进行朝会,一起商议(苻坚)说:“自从我继承了祖业,过去三十多年了,四方都渐渐安定,只有东南方的那个小地方,还没有蒙受君王的教化,现在大概的估算我的士兵,可以得到九十七万人,我想以自己为统帅去征讨他们,怎么样?”秘书监朱肜说:“陛下行驶的是上天的惩罚,必然是有征无战。晋国的君主如果不将玉玺悬挂在城门的上面,肯定会逃跑往海上客死他乡。陛下收复中国的土地人民,让他们恢复耕织,然后回御驾东巡,将成功告慰岱宗,这是千年才有的时机啊。”苻坚高兴的说:“这就是我的愿望啊。”尚书左仆射权翼说:“过去商纣王无道,但微子、箕子、比干三位仁人在朝,周武王尚且因此回师,不予讨伐。如今晋朝虽然衰微软弱,但还没有大的罪恶,谢安、桓冲又都是长江一带才识卓越的人才,他们君臣和睦,内外同心,以我来看,不可图谋!”苻坚沉默了许久,说:“诸君各自发表自己的意见。”
太子左卫率石越说:“今年岁镇守斗(这句是真不懂应该是天文方面忽悠的话),福德都在吴(江南)那一边,攻打他们必然有上天的灾祸(估计是血吸虫病),而且他们拥有长江的天险,人民都愿意跟随他为他所用。实在是不可以攻打他们啊。”苻坚说:“昔日周武王攻打纣王,违背岁命和卜卦,天理不顺,如果武王不攻打的话,江山是否易主还不知道呢。吴王夫差和孙浩(一个是战国时期一个是三国时期的)都仗着有江湖的保卫,任然不能免于灭亡。现在凭借我的人马之多,将马鞭丢进长江,足够使它断流,又有什么天险让他去依仗的呢!”太子左卫率石越回答说:“被灭亡的三个君主都是荒淫无度的无道之君,因此敌人打败他们,比从地上捡起东西来还要容易,现在的晋国虽然没有德行(这个估计是贴金的话),但还没有大的罪行,希望陛下暂时按兵不动,积累粮谷,来准备对付他们的挑衅。”就这样群臣们各自诉说自己的观点,很长时间不能决定下来。苻坚说:“这就是所谓的在道路边建造房屋,多久都不能造起来(这个是个典故)。我应该由自己来决断。”众大臣都出去了,只留下了阳平公苻融。苻坚对他说:“自古决定大事的人,只不过一两个大臣而已。现在众说纷纭,只会白白扰乱人心,我打算与你一同决定此事。”苻融于是对苻坚说:“现在攻打晋朝有三个不利因素:天理不顺,这是其一;晋国自身没有灾祸,这是其二;我军征战频繁,士兵都已疲惫不堪,百姓也都心怀畏敌之心,这是其三。群臣当中说晋朝讨伐不得的人,全都是忠臣,但愿陛下能够听从他们的意见。”苻坚听罢脸色一变说:“你也是这样,我还能把希望寄托在谁身上呢!我有百万强兵,财物兵器堆积如山;我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国君,但也并非昏庸之辈。乘着捷报频传的时机,前去攻打垂死挣扎的国家,为何还要担心不能攻克呢?怎能再留下这些残敌,让他们久而久之成为国家的忧患呢!”苻融哭泣着说:“晋朝不可以消灭,这是很显然的事情。现在却要大举出动疲劳的军队,恐怕不会取得万无一失的成功。何况我所担忧的,还不止这些。陛下宠信供养鲜卑人、羌人、羯人,使们遍布京师,这些人都对我国有着深仇大恨。如果只留下太子和数万弱兵守卫京师,我担心会有不测变故在我们的心腹地区发生,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这只是我的愚钝见解,果真不值得采纳,那么王猛却是一时豪杰,陛下曾经时常把他比作诸葛亮,为何惟独不铭记他的临终遗言呢!”苻坚却仍然不听。一时间向苻坚进谏的大臣甚众,苻坚坚持说道:“凭借我们的实力攻打晋朝,权衡双方的强弱之势,犹如疾风扫秋叶一样,然而朝廷内外却都说不能攻打,这的确很令我百思不得其解!”这个就是我找到的部分自己翻译的,遗漏了什么可以在问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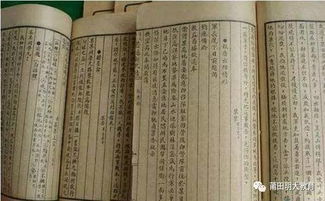
2.北齐书,第四十二卷,列传第三十四文言文翻译
北齐书原文: 王纮(hóng),字师罗,太安狄那人也,为小部酋帅。
纮少好弓马,善骑射,颇爱文学。性机敏,应对便捷。
年十三,见扬州刺史太原郭元贞,元贞抚其背曰:“汝读何书?”对曰:“诵《孝经》。”曰:“《孝经》云何?”曰:“在上不骄,为下不乱。”
元贞曰:“吾作刺史,岂其骄乎?”纮曰:“公虽不骄,君子防未萌,亦愿留意。”元贞称善。
年十五,随父在北豫州,行台侯景与人论掩衣法为当左,为当右。尚书敬显俊曰:“孔子云:‘微管仲,吾其被发左衽矣’以此言之,右衽为是。”
纮进曰:“国家龙飞朔野,雄步中原,五帝异仪,三王殊制,掩衣左右,何足是非。”景奇其早慧,赐以名马。
兴和中,世宗召为库直,除奉朝请。世宗暴崩,纮冒刃捍御,以忠节赐爵平春县男,赉帛七百段、绫锦五十匹、钱三万并金带骏马,仍除晋阳令。
天保初,加宁远将军,颇为显祖所知待。帝尝与左右饮酒,曰:“快哉大乐。”
纮对曰:“亦有大乐,亦有大苦。”帝曰:“何为大苦?”纮曰:“长夜荒饮不寤,亡国破家,身死名灭,所谓大苦。”
帝默然。后责纮曰:“尔与纥奚舍乐同事我兄,舍乐死,尔何为不死?”纮曰:“君亡臣死,自是常节,但贼竖力薄斫轻,故臣不死。”
帝使燕子献反缚纮,长广王捉头,帝手刃将下,纮曰:“杨遵彦、崔季舒逃走避难,位至仆射、尚书,冒死效命之士,反见屠戮,旷古未有此事。”帝投刃于地曰:“王师罗不得杀。”
遂舍之。 乾明元年,昭帝作相,补中外府功曹参军事。
皇建元年,进爵义阳县子。河清三年,与诸将征突厥,加骠骑大将军。
天统元年,除给事黄门侍郎,加射声校尉,四迁散骑常侍。武平初,开府仪同三司。
纮上言:“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,必当相与影响,南北寇边。宜选九州劲勇强弩,多据要险之地。
伏愿陛下哀忠念旧,爱孤恤寡,矜愚嘉善,舍过记功,敦骨肉之情,广宽仁之路,思尧、舜之风,慕禹、汤之德,克己复礼,以成美化,天下幸甚。” 五年,陈人寇淮南,诏令群官共议御捍。
封辅相请出讨击。纮曰:“官军频经失利,人情骚动,若复兴兵极武,出顿江淮,恐北狄西寇,乘我之弊,倾国而来,则世事去矣。
莫若薄赋省徭,息民养士,使朝廷协睦,遐迩归心,征之以仁义,鼓之以道德,天下皆当肃清,岂直伪陈而已!”高阿那肱谓众人曰:“从王武卫者南席。”众皆同焉。
寻兼侍中,聘于周。使还即正,未几而卒。
(原载《北齐书•25卷列传第17》有删节)译文: 王纮,字师罗,太安狄那人,是小部族的酋长。父亲王基,读书很多,有智谋\。
王纮年少时喜欢弓箭、马匹,善于骑马射箭,非常爱好文学。天性机智敏捷,应对灵活。
十三岁时,见到扬州刺史太原人郭元贞。元贞抚其背说:“你读什么书?”回答说:“诵读《孝经》。”
元贞说:“《孝经)讲的是什么?”王纮说:“地位在上的不骄纵,地位在下的不作乱。”元贞说:“我作刺史,难道骄纵吗?”王纮说;“公虽不骄纵,然而君子防患于未然,也希望留意此事。”
王贞称赞他。十五岁时,跟随父亲在北豫州,行台侯景和人谈论掩衣襟的方法是应当向左,还是应当向右.尚书敬显俊说:“孔于说:‘如果没有管仲,我们将头发披散不束,衣襟向左掩了。
’以此说来,衣襟向右掩是对的。”王纮进言说:“国家帝王即位于北方荒野之地,称雄中原,五帝三王的礼仪、制度各自不同。
衣襟向左或向右掩,哪里值得谈论它的是与非。”侯景惊奇他年少聪明,赐给他名马。
兴和年间,世宗召为库直,任奉朝请。世宗遇害突然去世,王纮冒死捍卫世宗,因忠节赐予平春县男的爵位,赏赐帛七百段、绫锦五十匹、钱三万和金带骏马,并任晋阳令。
天保初年,加授宁远将军,很为显祖重视优待。帝曾与左右的人饮酒,说:。
大乐痛快啊。”王纮说:“也有大乐,也有大苦。”
帝说:“什么是大苦?”王纮说:“长夜荒饮而不醒悟,国破家亡,身死名灭,就是所说的大苦。”帝默然不语。
后来责备王纮说:“你与纥奚舍乐共同事奉我兄,舍乐为我兄死,你为何不死!”王纮说:“君亡臣死,自然是正常的礼节,但贼\人力气小,砍得轻,所以我没有死。”帝让燕子献反绑王纮,长广王抓住头,帝手举刀将要砍下。
王纮说:“杨遵彦、崔季舒逃走躲避,职位达到仆射、尚书,冒死效命的贤士,反而被杀戮,旷古未有这样的事。”帝将刀扔到地上说:“王师罗不能杀。”
于是放了他。 乾明元年,昭帝作相,补任中外府功曹参军事。
皇建元年,晋升为义阳县子的爵位。河清三年,与诸将征伐突厥,加授骠骑大将军。
天统元年,任给事黄门侍郎,加授射声校尉,四次升任至散骑常侍。武平初年,任开府仪同三司。
王纮上书说:“突厥与宇文男来女往,必定相互呼应,从南北两个方面入侵边境。应当选派九州的勇士和善射之人,据守险要之地。
我愿陛下哀怜顾念忠诚的老臣,热爱抚恤孤寡之人,同情奖励忠实善良之士,忘记他们的过失,牢记他们的功劳,使骨肉之情更亲密和睦,使宽厚仁爱之路更广阔,追思尧、舜之风,仰慕禹、汤之德,克己复礼,以成大治,这是天下的幸事。” 武平五年,陈人入侵淮南,皇帝命令众官共同商议防御之策。

3.文言文不角事仆射的翻译
唐刘仁轨为左仆射,戴至德为右仆射,皆多刘而鄙戴。时有一老妇陈牒,至德方欲下笔,老妇顾左右曰:"此刘仆射?戴仆射?"左右以戴仆射言。急就前曰。"此是不解事仆射,却将牒来。"至德笑,令授之。戴仆射在职无异迹,当朝似不能言。及薨后,高宗叹曰:"自吾丧至德,无所复闻,当其在时,事有不是者,未尝放我过,因出其前后所陈,章奏盈箧,阅而流涕,朝廷始追重之。(出《国史异纂》)
【译文】
唐高宗时,刘仁轨做左仆射,戴至德做右仆射。大家都尊崇刘仁轨而鄙视戴至德。当时有一位老妇人呈递申述状,戴至德刚要下笔批示。老妇人向左右的人们问,这是刘仆射还是戴仆射?属下告诉她这是戴仆射。老妇人忙上前说:"这是不管事的仆射,把诉状还给我。"戴至德一笑,让人把诉状还她。在职期间,戴至德没什么明显的业绩。在皇帝和同僚面前,也不善于言词。他死后,唐高宗很痛惜。说:"自从我失去戴至德,再也听不到意见了。他在的时候,我有不对的地方,从不放过。"高宗把戴至德陈事的奏章拿出来,竟有满满的一匣子。高宗一边看一边流着眼泪,大家才知道戴至德是这样一位值得尊重的人
4.苏世长讽谏 全文翻译
翻译 武德四年,高祖平定王世充后,他的行台仆射苏世长带着汉南来归顺。
高祖责备他归顺迟了。苏世长叩首说:“自古以来帝王登基,用擒鹿作比喻,就是一个人得到了,其他人便收手了。
哪里有捕获鹿以后,还忿恨其他同猎的人,追究他们争夺鹿的罪名呢?”高祖和他有旧交,便一笑而过。 后来苏世长与高祖在高陵围猎,那天收获丰富,(高祖命令)将捕获的禽兽陈列在旌门。
高祖环顾四周的诸位大臣问:“今天围猎快乐吗?”苏世长回答说:“陛下打猎,荒废了政务,不足百日,没什么太值得高兴的!”皇上吃惊得脸色都变了,然后笑着说:“你发疯了吗?”苏世长回答说:“如果仅从我的角度来考虑便是发狂了,但如果从您的角度来考虑则是一片忠心呀!” 苏世长曾经在披香殿侍候皇上用餐,酒喝到高兴的时候,上奏道:“这座宫殿是隋炀帝建的吧?这是如何奢华的装饰呀!”高祖回答说:“你喜欢进谏像是个直率的人,其实内心狡诈。你难道不知道这座宫殿是我建的,何必(佯装不知而)怀疑是隋炀帝建的呢?” 苏世长回答说:“我真的不知道,但是看见倾宫、鹿台,琉璃做的瓦片,不是一位崇尚节俭的君王所应做的。
如果真是您建造的,实在不应当呀!我当初是一介武夫,有幸做您的侍从,见到您的住所只不过能够用来遮蔽风霜,在那时您也认为那样的住所也就足够了。如今因为隋炀帝的奢靡,百姓不堪忍受而造反,您得到了江山,其实是对他竭尽奢靡的惩罚,(您自己也应)不忘节俭呀。
现在在他的宫殿内又大加装饰,想革除隋的暴政,怎么办得到?”注释 平:平定 以汉南归顺:带着 高祖责其后服:责备 高祖责其后服:迟,晚 高祖责其后服:降服,归顺。 世长稽首:叩首 自古帝王受命:从古至今 自古帝王受命:受天命,意为登基 万夫敛手:收,停 遂笑而释之:表修饰。
后从猎于高陵:在 是日大获:这 陈禽于旌门:陈列 今日畋:打猎 陛下废万机:停下 陛下废万机:各类繁杂事务 不满十旬:百天 未为大乐:是 狂态发耶:发狂,发癫 何须诡疑:哪里必要假装 倾宫、鹿台:高耸的宫殿和楼台。鹿台:纣王所修的台。
这里披香殿的台。 并非帝王节用之所为也:节约开支 诚非所宜:应当。
见陛下宅宇才蔽风霜:只能 当此时亦以为足:也 当此时亦以为足:认为 今因隋之侈:奢侈 今于隋宫之内:在。 欲拨其乱,宁可得乎:想革除隋的暴政,怎么办得到?。
5.《北京书·袁聿修传》文言文译文
北齐书!袁聿修,字叔德,陈郡阳夏人。
他是北魏中书令袁翻的儿子,但过继给叔父袁跃为子。七岁时父亲去世,他守丧时的起居礼度,与成人相仿。
九岁时,州里辟署他为主簿。性格深沉而有见识,清净寡欲,与物无争,深受尚书崔休的赏识。
魏孝武帝大昌中,他初次任官为太保开府西阁祭酒。十八岁时,领本州中正。
不久,兼尚书度支郎,还历任五兵郎中、左民郎中。东魏孝静帝武定末,任太子中舍人。
北齐文宣帝天保初,任太子庶子,以本官行博陵太守。他任职数年,大有政绩,声誉颇佳,得到远近百姓的称赞。
天保八年,兼太府少卿,不久,转任大司农少卿,又改任太常少卿。北齐孝昭帝皇建二年,他因母亲去世而离职,不久,朝廷下诏命令 恢复前职,先后加冠军将军、辅国将军,调任吏部郎中。
时间不长,迁任司徒左长史,加骠骑大将军,领兼御史中丞。司徒录事参军卢恩道私自借贷库钱四十万,用来聘太原人王乂的女儿为妻,而王氏已先收下陆孔文的聘礼作为定婚礼物,袁聿修由于是司徒府的首要僚佐,又是国家负责司法的官员,知道此事而不加弹劾,受到免去御史中丞的处分。
不久,迁任秘书监。 齐后主天统中,朝廷下诏命令袁聿修与赵郡王高睿等商议制定五礼。
后出任信州刺史,就是他的本乡,当时人都认为是荣耀。他为政清静,不言而治,自从长吏以下,直到鳏寡孤幼,袁聿修都能得到他们的欢心。
后主武平中,御史都出来巡视诸州,梁、郑、变、豫等州与信州疆域相接,在信州的周围,御史都检举揭发出官员的不法行为,而御史竟然不到信州来,足见袁聿修所受到的信任。到他任满解职还京时,包括僧人在内的全州百姓,追来送别的填满道路,有人带来美酒与肉脯,哭泣着留连不舍,都想要运送。
当时正是盛暑,袁聿修恐怕百姓们过于劳累,往往为送行的人停下马,随手喝一杯酒,表示已领受他们的好意,感谢他们的情义,并 让他们回家。袁聿修回京后,信州百姓郑播宗等七百余人请求为他立碑,收敛嫌布数百匹,托中书侍郎李德林来撰写碑文以记述他的功德,有关部门为此上奏,后主下诏同意。
不久,他被任为都官尚书,仍领本州中正。转任兼吏部尚书、仪同三司,不久,被正式任命为吏部尚书。
袁聿修自小平和温润,在土族高门子弟中,最有规矩法度。他以名门之子历任清要官职,当时名士多很赏识他,称许他的风采与见识。
他在郎署的时候,正好赵彦深为水部郎中,同在一院,就结为朋友。赵彦深以后遭到淘汰,被遣放回家,由于无人拜访,大门口都长上杂草,而袁聿修还以旧情,到赵彦深家探问往来。
赵彦深得到重用后,仍感念甚深,因此,袁聿修历任要职,虽然是由于自己的才干声望,但也与赵彦深的援引有关。袁聿修任吏部尚书后,自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声望而得任此职的。
起初,冯子琼以尚书仆射掌管官员选任的事务,他子女的婚嫁之事,接连不断,袁聿修曾加以嘲讽,说:“冯公经营婚事,日不暇给。”等到袁聿修自己在吏部,也不能免于此,当时认为是由于所处的地势而决定的。
他在官廉洁谨慎,当时少有。东魏、北齐时期,尚书台郎多不免于相互送礼,袁聿修在尚书十年,没有接受过别人一升酒的馈赠。
尚书邢邵与袁聿修有旧交,每次在尚书省开玩笑时,常称袁聿修为清郎。武成帝大宁初,袁聿修以大常少卿出使巡察,并受命考核官员的得失。
他经过兖州时,邢邵正担任兖州刺史,两人分别后,邢邵派人送去白纳为信。袁聿修退还白纟由不受,与邢邵写信说:“今日经过您处,与平日出行不同,瓜田李下,必须避嫌,古人对此是十分慎重的。
人言可畏,应象防御水患一样,不忽视细微末节,愿您体会此心,不至于重责。”邢邵也欣然领会,回信说:“先前的赠送,过于轻率,未加考虑,老夫匆忙之间,没有想到这个问题。
敬承来信之意,我并无不快。弟昔日为清郎,今日复作清卿了。”
到袁聿修在吏部,正赶上国政衰败,道德沦丧,如果违背权要之臣,恐怕立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,袁聿修虽然自己仍严守清白,但还是不能摆脱请谒的烦劳。 北齐灭亡后,他入仕北周,任仪同大将军、吏部下大夫。
周静帝大象末,为东京司宗中大夫。隋文帝开皇初,加上仪同,迁任东京都官尚书。
东京废,又入朝任都官尚书。开皇二年,出任熊州刺史,不久即去世,时年七十二岁。
他儿子袁知礼,北齐后主武平末官至仪同开府参军事。隋文帝开皇中,袁知礼为侍御史,历任尚书民部、考功侍郎。
隋杨帝大业初,他死于太子中舍人任上。
6.文言文翻译
《晋书•嵇绍传》【原文】 嵇绍字延祖,魏中散大夫康之子也。
十岁而孤,事母孝谨。以父得罪,靖居私门。
山涛领选,启武帝曰:“《康诰》有言‘父子罪不相及。’嵇绍贤侔谷缺,宜加旌命,请为秘书郎。”
帝谓涛曰:“如卿所言,乃堪为丞,何但郎也。”乃发诏征之,起家为秘书丞。
绍入洛,累迁汝阴太守。尚书左仆射裴颜亦深器之,每曰:“使延祖为吏部尚书,可使天下无复遗才矣。”
沛国戴晞少有才智,时人许以远致,绍以为必不成器。晞后为司州主簿,以无行被斥,州党称绍有知人之明。
元康初,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时侍中贾谧以外戚之宠,年少居位,潘岳、杜斌等皆附托焉。
谧求交于绍,绍拒而不答。及谧诛,绍时在省,以不阿经凶族,封弋阳子,迁散骑常侍。
太尉、广陵公陈准薨,太常奏谥,绍驳曰:“谥号所以垂之不朽,大行受大名,细行受细名。自顷礼宫协情,谥不依本。
准谥为过。且谥曰缪。”
事下太常。时虽不从,进行惮焉。
齐王冏既辅政,大兴第舍,骄奢滋甚,绍以书谏曰:“夏禹以卑室称美,唐虞以茅茨显德,宜省起造之烦,深思谦损之理。”冏虽遂顺以报之,而卒不能用,绍尝诣冏谘事,遇冏宴会,召董艾等共论时政。
艾言于冏曰:“嵇侍中善千丝竹,公可令操之。”左右进琴,绍推不受。
冏曰:“今日为欢,卿何吝此邪?”绍对曰:“公匡复社稷,当轨物作则,垂之于后。绍虽虚鄙,忝备常伯,腰绂冠冕,鸣玉殿省,岂可操执丝竹,以为伶人之事!”若释公服从私宴,所不敢辞也。
冏大惭。艾等不自得而退。
寻而朝廷复有北征之役,征绍。绍以天子蒙尘,承诏驰诣行在所[注]。
值王师败绩于荡阴,百官及侍卫莫不溃散,唯绍俨然端冕,以身捍卫,交兵御,飞箭雨集,绍遂被害于帝侧,血溅御服,天子深哀叹之。及事实,左右欲浣衣,帝曰:“此嵇侍中血,勿去。”
(节选自《晋书·嵇绍传》)[注]行在所:天子所在的地方。 【译文】 嵇绍,字延祖,曹魏中散大夫嵇康之子。
十岁时失去父亲,奉养母亲孝顺慎重。武帝下诏书征用他,离家做秘书丞。
嵇绍刚到洛阳,有人告诉王戎说:“昨日在人群中曾见到嵇绍,看他气宇轩昂,恰如野鹤立在鸡群中。”王戎说:“你还未见过他父亲呢。”
尚书左仆射裴頠(wěi)也很器重他,常说:“如果让嵇延祖任吏部尚书,可使天下不会再遗漏人才了。”沛国的戴晞年轻有才气,同嵇绍的侄儿嵇含相互交好,当时人们相信他将来必有大用,嵇绍却认为他一定不会成大器。
戴晞后来任司州主簿,因为行为不端被驱逐,州里民众都说嵇绍有知人之明。后转任豫章郡内史,因母亲去世,未到任。
元康初年(291),任给事黄门侍郎。当时侍中贾谧凭借着受宠爱的外戚的身份,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,潘岳、杜斌等人都依附他。
贾谧请求与嵇绍交好,嵇绍拒绝不理。等到贾谧被处死,嵇绍正在官署,因为他不亲附恶人,被封为弋阳子,又升为散骑常侍,兼任国子博士。
太尉、广陵公陈准死了,太常奏请加给谥号,嵇绍反驳说:“谥号是用来使死者垂名不朽的,大德之人应当授予大名,微德之人就应授予微名,“文武”这些谥号,显扬死者的功德,“灵厉”这些谥号,标志着死者的糊涂昏昧。由于近来掌礼治之官附和情弊,谥法便不依据原则。
加给陈准的谥号过誉,应该加谥号为‘缪’。”这件事交给太常处理。
当时虽然没有听从嵇绍的意见,但是朝廷大臣都有些惧怕他。 不久嵇绍被征召为御史中丞,未拜受,又任侍中。
河间王司马颙、成都王司马颖起兵直驱京都,借以讨伐长沙王司马乂,帝王车驾驻扎城东。司马乂向属众宣告说:“今日西征,希望谁作都督呢?”军中将士都说:“希望嵇侍中尽力在前面引导,我们虽死犹生。”
于是授予嵇绍使持节、平西将军。继而司马乂被俘,嵇绍重任侍中。
公王以下的官员都到邺城向司马颖认罪,嵇绍等人均被罢官,免为平民。不久朝廷又有向北征伐的战役,征召嵇绍,恢复了他的爵位。
嵇绍因天子蒙受风尘,接奉诏书驰往行驾住处。恰逢王师在荡阴战败,百官及侍卫人员都纷纷溃逃,只有嵇绍庄重地端正冠带,挺身保卫天子,军队接近鸾驾,飞箭如雨,嵇绍于是被射死在皇帝的身旁,鲜血溅染了御衣,天子为他的死沉痛悲叹。
等到战事平定,侍从要浣洗御衣,皇帝说:“这是嵇侍中的血,不要洗去。”。
7.孝其名物度数 以补毛儒之未备
“读《诗集传》,有《名物钞》八卷,正其音释,考其名物度数,以补先儒之未备。”
出自《元史·许谦传》。意思是:他读《诗集传》便写《名物钞》八卷,为它正音解释,进行考证,以补先儒书中不完备之处。
以下全篇译文及原文供参考: 译文: 许谦字益之,祖籍京兆。他的九世祖许延寿是宋朝刑部尚书。
以后各代都任官。后由平江迁至婺州路之金华,到谦时已是五代为金华人了。
谦几岁时,父亲早逝,刚能说话,伯母陶氏口授《孝经》《论语》,他的记忆力很强。稍大一点,对学习极为努力,自己规定内容进行学习,取四部书,分昼夜阅读,即使有病也不停止。
在金履祥的门下求学,履祥教育他说:“你们求学就像五味调合,加了醋酱后,味道立即不同。你来见我已三天,像个女子,羞于言辞,难道我的教学没能激发你吗?”谦听后非常敬畏他。
几年后终于领会了老师授课中的奥妙。他无书不读,即使微小的问题也不放过,哪怕不完整的文章或只字片语,从不忽视。
遇到不通之处,从不妄作解释;对先儒的话,自己不甘听从的,决不随便同意。他读完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写《丛说》二十卷,其中说:“学习要以圣人作为标准,先学他们的思想,再学他们做的事。
圣贤的思想都在《四书》里,其要义全在朱子注释中。但他的辞简而意义深广,读的人怎么可能不学其思想就理解其真义呢?”他读《诗集传》便写《名物钞》八卷,为它正音解释,进行考证,以补先儒书中不完备之处,但仍保存其原意,通过旁征博引,以自己的见解作结论。
读《书集传》,著《丛说》六卷。读历史著《治忽几微》。
他采用编年体,著史书,上起太..氏,下止宋元..元年(1086)九月司马光卒,说明历代兴亡的原因。 他还著有《自省篇》,白天做的事,夜晚一定写下来,不能写的一定不做。
对天文、地理、典章、食货、刑法、字学、音韵、医经、术数等学说,无不通晓。对有关释家、老子学说,也要探其奥秘。
他曾说“:读书人谁不说要排除异端,但能探其奥妙,辨别异同是非的人又有几个呢?”又给《九经》、《仪礼》、《春秋三传》断句,对竹简顺序颠倒或抄写的错误,分别用铅黄和朱红划上,以示区分。以后吴师道买到吕祖谦点校的《仪礼》,与许谦校订的比较,不同之处仅有十三条。
谦不喜欢显露才华,除非有益经义,张扬道德和事理的,都不轻易动笔。 延祐初(1314),住东阳八华山,众多学生向他求教,不久便开门讲学,学生不远千里而来。
他教学生是诚心诚意,细致耐心,倾其所知,并以此为乐,孜孜不倦。在门下受教的学生千余人,他按各人的情况分别教授,使每人都有所得,但他从不用应科举的文章为教材。
谦孝顺父母,尊敬兄长,为人处事不拘泥于古人,不流于世俗。在家乡四十年,各处人士都以不访他为耻。
路过其乡的士绅都要去他家问安。有人向他求教,听过讲解的人,深为佩服。
大德中遭重灾。他说“:现在国家公私缺粮,饿死的人到处可见,我怎能只顾自己吃饱?”中州有名望的人廉访使刘庭直、副使赵宏伟对谦都深为佩服,要向朝廷推荐。
到晚年身负教学重任,远近的学生以他的身安否作为道的盛衰。至元三年(1337)卒,享年六十八岁。
朝廷谥号文懿。 先是何基、王柏及金履祥卒,他们的学问还没有发扬光大,至谦时他的思想更加突出,学生追本穷源,认为是朱熹的嫡传。
江浙行中书省替他向朝廷奏请求建“四贤书院”,来奉祭祀,并排在学官之列。 履祥居仁山之下,学者因称为仁山先生。
大德中卒。元统初,里人吴师道为国子博士,移书学官,祠履祥于乡学。
至正中,赐谥文安。 原文: 许谦,字益之,其先京兆人。
九世祖延寿,宋刑部尚书。八世祖仲容,太子洗马。
仲容之子曰洸、曰洞,洞由进士起家,以文章政事知名于时。洸之子寔,事海陵胡瑗,能以师法终始者也。
由平江徙婺之金华,至谦五世,为金华人。父觥,登淳祐七年进士第,仕未显以殁。
谦生数岁而孤,甫能言,世母陶氏口授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,入耳辄不忘。稍长,肆力于学,立程以自课,取四部书分昼夜读之,虽疾恙不废。
既乃受业金履祥之门,履祥语之曰:“士之为学,若五味之在和,醯酱既加,则酸咸顿异。子来见我已三日,而犹夫人也,岂吾之学无以感发子耶!”谦闻之惕然。
居数年,尽得其所传之奥。于书无不读,穷探圣微,虽残文羡语,皆不敢忽。
有不可通,则不敢强;于先儒之说,有所未安,亦不苟同也。 读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有《丛说》二十卷,谓学者曰:“学以圣人为准的,然必得圣人之心,而后可学圣人之事。
圣贤之心,具在《四书》,而《四书》之义,备于朱子,顾其辞约意广,读者安可以易心求之乎!”读《诗集传》,有《名物钞》八卷,正其音释,考其名物度数,以补先儒之未备,仍存其逸义,旁采远援,而以己意终之。读《书集传》,有《丛说》六卷。
其观史,有《治忽几微》,仿史家年经国纬之法,起太皞氏,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书左仆射司马光卒。备其世数,总其年岁,原其兴亡,著其善恶。
盖以为光卒,则中国之治不可复兴,诚理乱之几也。故附于续经而书孔子卒之义,以致其意焉。
又有《自省编》,昼之所为,夜必。
8.钟离意字子阿翻译
钟离意字子阿,会稽山阴人也。少为郡督邮。时部县亭长有受人酒礼者,府下记案考之。意封还记,入言于太守曰:“《春秋》先内后外,《诗》云‘刑于寡妻,以御于家邦’,明政化之本,由近及远。今宜先清府内,且阔略远县细微之愆。”太守甚贤之,遂任以县事。建武十四年,会稽大疫,死者万数,意独身自隐亲①,经给医药,所部多蒙全济。
举孝廉,再迁,辟大司徒侯霸府。诏部送徒诣河内②,时冬寒,徒病不能行。路过弘农,意辄移属县使作徒衣,县不得已与之,而上书言状,意亦具以闻。光武得奏,以〔视〕霸③,曰:“君所使掾何乃仁于用心?诚良吏也!”意遂于道解徒桎梏,恣所欲过,与克期俱至,无或违者。
后除瑕丘令。吏有檀建者,盗窃县内,意屏人间状,建叩头服罪,不忍加刑,遣令长休。建父闻之,为建设酒,谓曰:“吾闻无道之君以刀残人,有道之君以义行诛。子罪,命也。”遂令建进药而死。二十五年,迁堂邑令。防广为父报仇,系狱,其母病死,广哭泣不食。意怜伤之,乃听广归家,使得殡敛。丞掾皆争,意曰:“罪自我归,义不累下。”遂遣之。广敛母讫,果还入狱。意密以状闻,广竟得以减死论。
显宗即位,征为尚书。时交趾④太守张恢,坐臧千金,征还伏法,以资物簿入大司农,诏班赐群臣。意得珠玑,悉以委地而不拜赐。帝怪而问其故。对曰:“臣闻孔子忍渴于盗泉之水。此臧秽之宝,诚不取拜。”帝嗟叹日:“清乎尚书之言!”乃更以库钱三十万赐意。转为尚书仆射。
文言文译文:
钟离意字子阿,会稽山阴人。年青时做过郡府督邮。当时他管辖的县里有个亭长受人酒礼,府吏将这情况登记在文符上(以备)审察。钟离意封还簿册后,进郡府对太守说:“《春秋》主张先内后外,《诗经》说‘对嫡妻(自己要)作为祟礼法的典范,以影响对于家邦的治理。’明了治政教化的根本,(则能)由近及远。现今应当先清理府内,暂且宽缓巡行(稽查)远县细微的过失。”太守认为他很能干:,就委任他管县里的事。建武十四年(公元39年)会稽瘟疫大爆发,病死的人以万计数,钟离意只身(赴疫区)亲自抚恤(难民),供给医药,他所管辖地区大都蒙受救济。
钟离意被举荐为孝廉,再次升迁,应召到大司徒侯霸公府供职。他奉诏指挥解送囚徒到河内,时值冬寒,囚徒患病不能行走。路过弘农县时,钟离意便传下文书让县里替囚徒制做衣服,县里不得已给囚徒制作了衣服,但上书朝廷奏明此事。钟离意也将全部情况上报,让皇帝了解(实情)。光武帝见到奏章后,将奏章给侯霸看,并说:“你任用的属下怎么如此尽心仁义呢?这个人的确是良吏。”钟离意又在路上解除囚徒的枷锁,任凭他们到想探访的地方去,(但与囚徒约定)在规定的日期都要到达(目的地),(结果)没有人违约。
后来,钟离意被授职作瑕丘县令。县吏中有个叫檀建的,偷窃县衙里的东西,钟离意屏退左右悄悄地询问,檀建叩头服罪,钟离意不忍心施以刑罚,便遣送他回家,令他长期赋闲。檀建的父亲了解(真相后),为檀建安排了酒席,对他说:“我听说无道之君用刀杀人,有道之君用义杀人。你的罪过当以命抵。”于是令檀建服药而死。建武二十五年(公元50年)。钟离意调任堂邑县令。县民防广为父报仇,吃了官司。他的母亲病亡,防广哭泣不食。钟离意哀怜他,于是(打算)任凭防广归家,使他能为母亲办丧事。属下都规谏钟离意(认为不宜这样处理),钟离意说:“罪人是由我释放的,(此举合宜道义)不会连累你们。”于是就把防广放走了。防广安葬母亲后,果然回来坐牢。钟离意暗中将此事上报,使上司知道此事,防广最终被免除死罪。
显宗即位,钟离意被征拜为尚书。这时交趾太守张恢,因贪赃千金,被追究押回京师伏法。(贪贿的)钱物等记录在案,(一并)没收,交予大司农。朝廷下诏将这些财物分赐给群臣。钟离意得到珠宝,将(珠宝)全部放到地上而不接受赏赐。显宗很奇怪,便问他这样做的原因,钟离意回答说:“我听说孔子忍耐着干渴,也不饮盗泉的水。这些贪赃受贿得到的宝物,(我)确实不敢接受。”显宗感叹道:“尚书的话真清正啊!”于是改变作法,赐给钟离意库钱三十万。又将他提升为尚书卜射。
不好意思,我全部都贴上了,见谅
9.《新世说》食而去稗 原文及翻译
原文: 曾涤生驻军安庆,有戚某自田间来。
行李萧然,农服敞素,对人沉默不能言。曾颇爱之,将任以事。
一日会食,值饭有稗粒,某检出之而后食。曾默然,旋备资遣之行。
某请其故,曾规之曰:“子食而去其稗。平时既非豪富,又未曾作客于外,辍耕来营不过月余,而既有此举动。
吾乡人宁复如是耶?吾恐子之见异思迁,而反以自累也。”译文:曾国藩驻军安阳时,一个亲戚从乡村来投奔。
带的行李很少,衣着简朴,不爱说话。颇得曾国藩所爱,曾国藩打算为他谋一份差事。
某天他们一起吃饭,恰巧饭里有稗子,这亲戚先把稗子挑了出来,然后才吃。曾国潘沉默不语,不久就拿出盘缠让他离开。
亲戚不解问曾国潘原因,曾国潘规劝他:你吃饭事把稗子挑了出来然后才吃,平时又不是有钱人,又没寄居异地,离开农村来我这不过一个多月,就有这种行为,我的老乡难道都是这样吗?我怕你见异思迁,反而害了自己啊。



